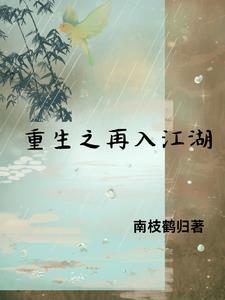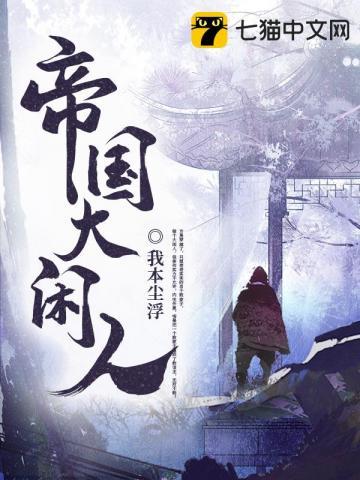笔趣乐>唐末:从一介书生到天下共主 > 第73章 太监(第1页)
第73章 太监(第1页)
全都退社了?”
“都退了,就剩我们几个。”
“也好,剩下的都是真朋友。”
“……”
李佑被取消童生的消息传出后,原本三十四个大同社成员,短短两天之内便退得只剩寥寥几人:徐瑜、苏如璋、苏如鹤、苏元德、刘子仁和林渊。
倒也没有其他复杂原因,无非是众人羞于与家奴身份的李佑为伍。
当然,大家的说辞都比较委婉,并未当面与李佑翻脸,只是纷纷找各种借口表明自己无暇参与社团活动。
苏如鹤这个有些古怪的人,已经许久没来书院,声称回家潜心钻研《齐民要术》——他在研读《论语集注》时,对其中关于农事的记载产生兴趣,进而对各类农书典籍着迷。
苏如鹤同样消失了半个多月,正软磨硬泡让家里为他聘请骑射老师。
李佑将精钢枪头用布仔细裹好,以长枪当作拐杖,在纷飞的大雪中艰难前行,准备去跟山长苏元禄辞别。
这杆长枪的枪杆是用檀木制成,檀木生长缓慢,且易长歪,寻常农民都不舍得砍伐,一根檀木制成的枪杆价值颇高。
至于白蜡杆,在民间用于比武尚可,若用于战场厮杀就有些不切实际了——“以岭南檀木为上,乌木次之。红桦劲而直,然易碎。白蜡质软,适为棍材。”
真正顶级的战场长枪,皆为复合材料打造:以坚韧木材为芯,外裹皮革,再缠绕铜丝与绳索。
“咯吱,咯吱……”
李佑一脚深一脚浅,在厚厚的积雪中蹒跚挪移,若不拄着这根棍子,还真难以借力。
今年的雪,下得格外猛烈,张守义居住的茅草屋顶,都被积雪压塌了。张夫子无奈,只能搬到私塾去住,若继续独居,恐怕晚上会被活活冻死。
短短几日,颍上县便已有不少人被冻死。
“咚咚咚!”
李佑抖落身上的雪花,将长枪斜靠在墙壁上,抬手轻轻敲响了房门。
“进来。”屋内传出苏元禄的声音。
李佑推门而入,恭敬说道:“小子拜见山长。”
苏元禄微笑着问道:“怎么不自称晚生了?”
“童生身份已被除名,小子已不配如此自称,”李佑拱手说道,“小子此番前来,是向山长辞行的。”
“唉!”
苏元禄一声长叹,说道:“我并未赶你下山,若你喜爱读书,依旧可在书院旁听。”
李佑说道:“小子如今是鼎盛楼的二掌柜,此前多有懈怠,往后需更加勤勉才是。”
“也罢,”苏元禄说道,“做酒楼掌柜,也算是个不错的营生,只是莫要荒废了诗书。”
“小子定当谨遵教诲,”李佑作揖说道,“就此告辞。”
苏元禄意兴阑珊,挥了挥手说:“去吧。”
除了铜钱和书稿,李佑什么都没带,也没有惊动任何人,拄着长枪独自下山而去。
风雪如刀,刮在脸上生疼,李佑还不时因积雪太深而踩空跌倒,但他的心情却格外愉悦,仿佛一只挣脱牢笼,重获自由的飞鸟。
再过四个月,他就满十五岁了,按照大唐虚岁的算法,便是十六岁。
鼎盛楼二掌柜这个身份,是李佑给自己预留的退路。他既能借此一边打工赚钱,一边结交三教九流之人,等待时机,静观天下局势的变化。
即便在这寒冬腊月,管仲镇依旧热闹繁华,只要颍水和其支流不被冰封就行。
“哥哥,你来啦!”绘彩热情地打招呼,如今他已是酒楼的账房先生。
李佑将长枪靠在柜台内侧,问道:“这几日生意如何?”
绘彩无奈地叹口气:“生意还算凑合,只是门摊税又涨了。”
李佑苦笑着说:“朝廷缺钱,什么税能不涨呢?”
“这次涨得也太多了,”绘彩压低声音说道,“前些日子,县里来了个宦官,专门负责催税,连县令都拿他没办法。”
“当今圣上,倒颇有玄宗爷当年的做派。”李佑调侃道。
在开元盛世之后,市面上税种繁杂,有门摊税、行市税、商货税等等。由于宫中大肆开设皇店,宦官肆意摊派,致使税种愈发五花八门。
到了本朝初期,大力改革,将各税合并,统一征收“门摊税”。
这种门摊税以县为单位,规定各县应缴纳的税额。县令依据应收税额,让县城与市镇分摊,每个季度征收一次,年底再运往课税署,由课税部门层层上缴至中央。
而如今,局势愈发紧张,圣上如同当年玄宗后期,派出税使四处催税,手段强硬。
当时最让人恐惧的是矿税,宦官只要瞧着哪家富裕,便诬陷其家中有矿,若不赶紧补缴税款,就直接抓人,搞得无数人家破人亡。
如今圣上被逼无奈,也效仿此法,派宦官到处催逼税款。
管仲镇的门摊税,年初就已经涨过一次,年底又传出还要再涨,而且那宦官直接跑到县衙施压。
宦官自然能捞得盆满钵满,县令也能跟着分一杯羹,下面的吏员们也能喝点汤,可受苦的却是店铺老板和小摊贩——实际上中央朝廷增收有限,大部分商税都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。
绘彩指着街面说道:“咱们酒楼还好,无非少赚些钱子,外面那些摊贩才是真的苦不堪言。”
李佑走到酒楼门口,左右环顾一番,回来后说道:“难怪感觉摊贩少了许多,这到底涨了多少税啊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