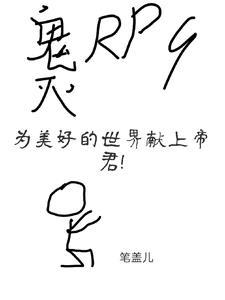笔趣乐>幽月仙母传 > 第11章 入界宜缓二(第1页)
第11章 入界宜缓二(第1页)
赤丹生缓缓抬起一只手,指尖没有任何光华流转,却有一股气息在凝聚。
那气息并不张扬,反而内敛到了极点,但西宫月毫不怀疑,当它爆时,足以将自己连同这片狭小的空间一同从世间抹去,不会留下丝毫痕迹。
西宫月闭上了眼睛。
不是认命,而是不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让恐惧玷污了自己眼中的决意。
她将脑海中那张稚嫩的面容清晰地勾勒出来,仿佛要将这最后的温暖带入黑暗。
她没有挣扎,也没有哀求,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终结的降临。能死在追寻儿子的路上,或许,也是一种归宿。
然而,预想中形神俱灭的痛苦并未到来。
西宫月惊疑不定地睁开眼,只见赤丹生已经收回了手,那张枯树皮般的老脸上,竟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神色。
他深陷的眼窝在她身上停留片刻,随即,他宽大的灰袍袖口随意一拂。
原本空无一物的洞府中央,随着一阵细微的空间涟漪荡漾开来,竟凭空出现了一张古朴的石桌和两张石凳。
石桌材质温润,似玉非玉,表面天然生成云水纹理,散着淡淡的清凉气息,瞬间驱散了洞府内的沉闷。
桌面上,一套紫砂茶具悄然浮现,茶壶嘴还袅袅飘起一缕若有若无的白气,带着奇异的茶香。
赤丹生自顾自地在其中一张石凳上坐下,那佝偻的身躯在石凳上显得愈渺小,他伸出干枯的手指,轻轻拂过茶壶。
西宫月警惕地看着赤丹生,以及那张突然出现的石桌。
赤丹生见她如此,也不催促,只是自顾自地拿起茶壶,往两个小巧的紫砂杯中注入碧绿色的茶水。
茶水落入杯中,竟出清脆悦耳的叮咚声,仿佛蕴含着某种奇妙的韵律。
茶香愈浓郁,那香气不似凡间任何茶品,闻之令人心神一清,连方才的恐惧与疲惫都消散了不少。
没有任何征兆,洞府内的光线骤然变得柔和而明亮,并非外界天光增强,而是源自洞府本身。
赤丹生倒茶的动作猛地顿住,那枯槁的身形瞬间绷直,他以一种与之前老态龙钟截然不同的敏捷站起身来,朝着面前空无一人的石凳深深地躬身行礼,姿态恭敬到了极点,甚至带着畏惧。
西宫月的心脏莫名一紧,下意识地顺着赤丹生行礼的方向望去。
然后,她看见了光。
不是洞外透进的微光,而是一种自虚空深处弥漫开来的清辉。那光很淡,很柔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,悄无声息地驱散了此地的阴森与昏暗。
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冷香,似雪后初绽的寒梅,清冽孤高,不容亵渎。初闻清冽,细品之下却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孤寂。
光芒的中心,一道身影缓缓凝聚,就连时间都仿佛凝固成了琥珀。
她穿着一袭再简单不过的月白道袍,宽大的袍袖自然垂落,衣料上看不出任何织锦纹绣,唯有在流动的清辉中,隐约可见袍角与袖缘处有银线勾勒出的细密云纹,如呼吸般明灭不定。
她的青丝用一根玉簪松松挽起,几缕垂落额前颈侧,更衬得那张脸愈惊艳,分明生得一副仙姿玉貌之颜,却冷得像万载玄冰雕琢而成。
她就那样静静地坐着,没有看西宫月,也没有看任何东西,仿佛只是恰好出现在这里,与这空间融为一体,又然于这一切之上。
西宫月屏住了呼吸。
她从未见过这样的人。
不,或许这根本不能称之为“人”。
对方身上没有流露出任何强大的气息,没有迫人的威压,但西宫月却从灵魂深处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与敬畏。
就像溪流仰望星空,蜉蝣面对沧海,那是一种生命层次上的绝对差距,无关力量,源于本质。
沈栖梧终于动了。
那双凤眸,深邃如同蕴含了整片冬夜的星空,平静无波,落在了西宫月身上。
目光相接的刹那,西宫月浑身一僵。
那目光并不锐利,却比世间任何神兵利器都要可怕。
它像是最柔和的月光,无孔不入地照了进来,穿透了她的皮肉,直接映入了她的神魂深处。
她感觉自己所有的记忆、恐惧,甚至那些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隐秘念头,都在这一眼下无所遁形,被看了个通透。
一股寒意从脊椎骨窜起,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。
但她没有退缩。
西宫月死死咬住下唇,用疼痛驱散那几乎要让她瘫软的恐惧,强迫自己站直身体,尽管身体正在不受控制地颤抖。
沈栖梧深邃的凤眸,一瞬不瞬地凝视着西宫月那双决绝的眼睛。
她在那双眼睛里,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火焰,看到了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的勇气,看到了一种……她曾经无比熟悉,却又在漫长岁月中几乎被磨平的东西。
西宫月粗重的喘息声,在死寂中格外清晰。
她浑身脱力,冷汗早已浸透单薄的衣衫,仿佛下一刻就会彻底散架。
但她依旧强撑着,没有让自己滑倒在地,目光依旧牢牢锁在沈栖梧身上。
沈栖梧静静地看了她很久,久到西宫月几乎以为时间真的停止了流动。